从深圳、广州的情形来看,进入到社区的专业社工,与原本就存在于社区的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一种奇怪的关系。
所谓原来的社区工作人员,各地名称不同,但实质大同小异。在深圳其载体为“社区工作站”,在广州则为“居委会”;无论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社区工作站站长(大部分情况下,这几个职务属于同一个人),还是社区专干(他们承担不同的管理或服务工作),他们都可以被体制称作社区干部,广州和其它个别城市也称之为“社工”,所以现在有了专业社工之后,在称呼上就有了一些混乱;严格意义上,他们都不属于体制内人员,因为他们不拥有体制内的编制(“公务员编”、事业单位“职员编”或“雇员编”),而只是一种准身份,比如广州叫“社工编”,而深圳则叫“员额编”(所谓拨款之数额是也,并不附着于具体人名),但是他们又明显属于稳定地吃皇粮的人,政府也很难开掉他们;事实上他们是附着于体制的人(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杂役),事实上承担了体制末梢的功能,居民往往视他们为、他们很多时候也自视为体制内人员或基层政府的代表。比如当有社区干部贪污而被处理时,无论是媒体或官方都会习惯用“社区官员”这个词来描述。
这个群体人员的来历五花八门,有的是街道办派下来(如社区党委书记)或发配下来的(原来街道办的临聘人员,开不掉,转到更基层做社区工作),有的是解决退伍军人或相关政策的就业问题而来,有的是各种关系介绍来吃皇粮的,有的则是城中村社区的干部(他们才真的具有“官”的权力与地位)。
对这个群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认为,他们长期深耕社区,与居民打成一片,熟悉和了解社区,具有强大的上门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社区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另一种则认为没有前面说的那么好,这些社区工作人员,更擅长的是应付上级检查评比考核,以及向居民做表面的宣传工作,以及用“管理”的思维来管控居民,他们缺乏专业知识,不具备解决很多新问题的能力和办法。
可能要让他们与进入社区的专业社工们进行较长时间的观察与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相对公允的判断,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刚好,就在广州、深圳的情形来说,目前老社干们与专业社工们共存于社区,可能还会共存较长一段时间,因此,新旧两类人固然会在社区内进行微妙的博弈,亦可视为一场业务竞赛,当然也可能构建一种合作模式。
对于专业社工们来说,他们拥有较强的理论和书本专业知识,同时由于大部分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工作有热情跟激情,而且善于创新工作方法,善于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工具,这些是专业社区们的优势。他们的劣势是,很多人不熟悉社区,要跟社区居民做到相互熟识,需要时间与沟通过程;其次他们不善于跟行政体系打交道,不懂官场潜规则;其三,社区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问题需要社会经验积累的情商,这一点更需要人生的积淀。
就当下的情形而言,专业社工,所做的更多是增量工作,即原来的社区工作重管理轻服务,社工依据社区服务中心的合约而来,做那些为居民增加的服务事项,这使得于原来的社区干部而言,他们像是一种补充或协助,因在上级政府(区、街道办)眼里,管理显然重要过服务,尤其是那些“控制性”的工作,“只能依靠体制内的人”。
一个不太好的苗头是,有些社区干部,因此视专业社区为辅助性人员,把自己分内事分派给他们去做,自己由此减轻了工作任务。这样的结果是,社工的专业性正在被弱化。长三角某城市甚至声称要“探索综合性社工”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社工被旧体制“异化”的危险信号。须知,“专业性”是社工的生命之所在,也是它能够将社区工作朝向专业性方向引领的基础,倘若同化在旧体制之中,等于我们终于又败坏了一种舶来新产品。
这也许需要我们评估“由社工服务机构整体承包社区服务中心或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模式,它是否是一种正确的方向。至于某些地方探索的将社区行政管理工作亦打包采购社工的方式,会对社工发展带来何样的影响,更需进一步讨论。
至于老的社区工作者与专业社工的理想协作模式,我想说,我还没有看到。我更希望看到旧的社区工作模式(管控)被新的模式(专业服务)所替代,但是在实操中,有太强大的反对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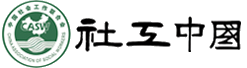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