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再现:两地社区协商平台的搭建
(一)苏州市G区: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的试点作为与新加坡政府合作的成功示范区,苏州市G区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有着丰富的成长经验。在人口结构上,G区辖区社区多为年轻化、知识水平高的高素质人群,然而在社区生活中却面临着居民参与水平不足,邻里互动逐渐减少的问题,城市社区内更像是一颗颗松散的“原子”,而非紧密联系的社会共同体。
G区结合两方面原因:辖区社区内的“原子群体”的现状,以及社区内广泛存在着诸如停车难、邻避困境等社区治理棘手问题,萌发了重塑社区治理格局的想法。2015年,G区社工委寻求当地高校专家团队的帮助,与辖区内Q社区一起,三方联手打造了“社区建设理事会”这一协商议事平台,更新了传统上“三驾马车”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建设理事会”协商议事平台自于Q社区试点开始,便体现着强大的汇聚民意、民情与群众参与感的功能,有效地整合了社区两委、草根精英、普通居民等多方主体的参与力量,让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编织成“网状”。2016年,该社区协商自治平台便推广至G区的11个社区里,随后,又不断扩散至几十个社区,呈现着良好的运行成效。
(二)扬州市H区: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的推广
扬州市H区不同于上文提及的苏州市G区,H区普遍属于村居合一型社区,年龄结构上,中年人口占大多数比重,在知识结构上,辖区居民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虽然两地社区人口结构差距较大,但是扬州市H区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社区居民参与感弱,社区疑难杂症逐渐增多而治理失效的困境。
在苏州市G区如火如荼开展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的同时,扬州市H区敏锐的嗅到了社区居民参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前景,于2019年6月与苏州市高校专家团队取得合作,在原有“社区建设理事会”平台基础上融入了当地特色的党建元素,共同打造了扬州市H区“红色物管会”社区协商自治平台,并于辖区三个社区内进行试点和推广。
有学者指出,根据经验研究的证据,目前城市社区中社会共同体的色彩逐渐消逝。社区居民只有中等强度的社区归属感,邻里互动逐渐减少,邻里关系的重要性日益下降,社区参与水平低下。的确,笔者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城市社区中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问题,如何增进社区内邻里之间的互动关系,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升居民的认同感与满足感,成为一项重大课题。苏州市G区和扬州市H区在社会治理上,创新地推出了协商议事平台,为我们研究该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有必要对该协商平台的运行机制和运作实效进行全面分析,从而总结经验,提升理性认知。
二、机制剖析:重塑城市社区生命的机理
苏州市高校专家团队从名称设计、机构设置、规则制定、技术应用、流程改善等方面入手,借鉴和整合了已有的开放空间技术、罗伯特议事规则、参与式预算、协商民意测验等协商民主技术和方法,与社区合作打造的协商议事平台,在其运行的每一环节都纳入了居民参与的元素,有效整合了群众资源。
(一)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
该协商议事平台目前形成了较为规范化的组织架构,即“党支部+四大理事+秘书”的模式,四大理事有理事长、常务理事、基础理事和名誉理事。理事长为社区书记,发挥牵头引导作用;常务理事主要由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人员组成,他们是协商结果的主要落实者;基础理事主要是社区居民小组长、楼道长以及热心居民等,他们是参与议事协商的主体;名誉理事主要是社区民警、城市管理者等相关职能部门成员;此外还配有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作为会议秘书,负责记录但不具有会议的投票表决权。另外,所有理事成员的确定都采取配额制而非选举制,并且定期更换。
在组织架构上,该协商平台不同于以往的社区治理平台,在组织成员上广泛的吸纳社区多元主体,确保了多方的可参与机制。早在进入二十世纪伊始,就有学者指出,行政化倾向是社区建设遭遇的重大挑战, 也是阻碍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在城市社区中,行政化色彩浓厚仍然对社区自治造成重大阻碍,阻滞了社区形成共同体的步伐。而破除这一行政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即扩大社区事务的多元参与机制,尤其是居民的广泛参与,重新构建居民与社区“传统三方”的信任关系。
(二)利益相关的议题收集
在多方主体协商讨论之前,按规则要进入议题收集环节。此环节内,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微信线上征集平台和基础理事成员,反映自己最为关心的问题和与自己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并且在协商议事会议召开之时,由相关主体依次提出本次会议的议题,包括议题背景、议题简要分析及解决方案等,主持人依次宣读各议题,逐个进行表决,若超过五分之四的理事同意,该议题直接通过,形成理事会决议。若未达到该比例,则正式进入议题协商讨论环节。
从以往的社区关系来看,传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不能很好的打入居民内部,社区居民之间亦由于情感的疏离而没有较多的深入交流,而代表广大居民利益的议题一旦提出,就将社区中的这两类关系拉近了。因为议题的提出,如:停车难、宠物扰民、邻避冲突等,都与居民自身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居民更加愿意参与到协商议事平台的讨论之中,居民之间也有了相应的“共同话题”。因此,在议题征集上,该协商平台既巧妙地调动了居民的积极性,又拉近了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文明民主的协商会议
进入会议讨论环节,由主持人按照议题内容主持讨论,宣读会议规则。在整场会议之中,对与会人员的发言有严格要求,如:交替发言、限时限次、一事一议、文明表达。参会人员的发言按照“谁先举手谁优先”的原则,不能无视会场秩序,另外,发言需要面向主持人,而不是面向其他参会理事成员。讨论结束后进行表决,超过半数理事同意即为通过,否则即为否决,讨论完成后,会议秘书根据会议结果形成会议决议,主持人现场宣读并提请各位理事审阅、签名。
会议过程中,凸显了协商、民主、文明、理性的色彩。笔者在实地访谈中了解到,无论是社区书记,还是社区居民,都对该协商议事平台表达了充分的肯定。苏州市H社区书记表示“这个平台就像是一个大碗,居民什么苦水都可以往里倒,它也可以容纳得了。”另有扬州市D社区居民表示“以前社区让我们来议事,大家都是来吵架的,各说各的话,谁也不让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不一样了,我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就发现在现在的协商议事平台上,有一些规矩的约束,大家都能坐下来为他人着想了,这是一个好的苗头。”的确,这样文明民主的协商议事会议更能够融合多元利益,包容各方观点。
(四)公开透明的反馈机制
由于参会人员仅是少部分代表,因此在形成会议决案后,动手实施之前,社区要将会议结果于社区公告栏以及居民群内广而告知,查看居民反馈意见和建议,调查决案是否充分反映民意。在得到大多数居民的认可之后,方可进入决案实施阶段。
公示阶段,居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对决案结果向社区居委会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社区会根据居民的反馈情况,对不符合民意的决案内容进行调整,进行再讨论。这样一来就充分保障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重大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居民在与社区“讨价还价”的互动过程中,能够感受到社区的“人情味”,加深了对于社区的认同感。最终,经由认同的产生和转化将共同生活的物理空间建构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地域共同体。
三、运行实效:协商平台运行的实际成效
该平台发展至今,体现了明显的运行成效,一方面,从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来看,决案的满意度更高,以往的棘手问题,如停车难问题,也通过协商讨论得到了逐步解决;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增强,社区逐渐培养了内在团结机制,从而有利于城市生活社会共同体的建立。
(一)显性成效:社区“疑难杂症”的有效解决
城市社区中的利益关系复杂多元,不少问题由于牵扯多方,而难以有效解决。自引入协商议事平台之后,这些堆积已久的问题逐步形成多方普遍关注的议题,被社区多元主体拿到明面上来协商讨论,经过一次次的协商会议,形成广泛的共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以苏州市D社区为例,D社区一直以来存在着“停车难”这一老大难问题,社区居委会无力改造,物业没钱改造,社区居民一直对此有所抱怨,这一问题的深入发展,也影响了小区的房价。自D社区2016年成立协商议事平台以来,一共经过了五次协商讨论,最终确立了社区停车位改造的“四步走”战略,2017年,该社区完成了停车位的改造工作,成功解决了社区的“老大难”问题。
(二)隐性成效:城市社区内在团结机制的培养
除了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这类显性成效,该协商议事平台还能够调动居民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激发居民交流自主性,培养社区内在团结机制,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凝聚力以及家园意识,推动社区实现自治。在组织架构上,由三元主体转变为多元主体;在议题收集、协商讨论、公示反馈的每一个环节都广泛采纳民意,培育理性意识,使得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充分沟通和互动,逐渐培养出一种团结机制,形成对社区的家园意识,重塑滕尼斯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
结语
城市社区是城市居民亲密接触的重要场域,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个“小社会”,但这一滕尼斯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往往由于一系列原因,处于解构之中。如何实现社区共同体的重塑对于我们今天的社区治理、城市社会发展以及国家社会整体的运行,都具有重大意义。笔者于本文提出的协商议事平台的构建,通过容纳多种社会管理力量参与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以实现社区关系的重构,只是其中的一种视角,对于城市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探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王德福.迈向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J].湖北社会科学,2022,428(08):38-46.
李达,张瑞才.社会治理共同体:一个文献述评[J].湖北社会科学,2021,No.411(03):56-66.
朱健刚.疫情催生韧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J].探索与争鸣,2020,366(04):216-223+291.
赵坤.风险社会中的共同体重建——兼论中国社会共同体治理的具体矛盾与治理智慧[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4(05):91-97.
蓝宇蕴.社会生活共同体与社区文化建设——以广州幸福社区创建为例[J].学术研究,2017(12):66-76.
李威利.党建引领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上海经验[J].重庆社会科学,2017(10):34-40.
栗明.社区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共容与权力架构[J].理论与改革,2017(03):114-121.
严志兰,邓伟志.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路径创新探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15(04):40-48.
刘岩,刘威.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J].浙江社会科学,2008(01):86-92+128.
桂勇,黄荣贵.城市社区:共同体还是“互不相关的邻里”[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6):36-42.
杨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意涵之探讨[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878-882.
杨荣.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J].探索,2003(01):5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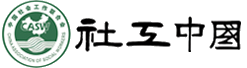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